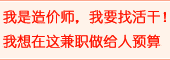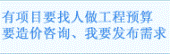Tulips Chen
时评:好的建筑,应该让人与人相遇
时间:2015-05-20 21:36来源: 作者: 点击:次
对外国建筑设计师并不陌生,只要在外滩地区转一圈,就能发现这座城市曾在近现代留下过许多外国建筑设计师的痕迹。仅一位邬达克,就在上海的29年间设计建成项目53个,其中25个先后被列为上海市优秀历史建筑。
如今,快速发展中的上海再次成为全球建筑师的向往之地。上海,藉由当代外国建筑师触摸当今世界建筑设计前沿思考,并由此获得与外国建筑文化沟通互动的机会,对这些建筑师而言,他们也通过上海实现了自己的抱负。
近日,我们走访了两位访沪的世界知名建筑设计师——以上海世博会“种子圣殿闻名天下的托马斯·赫斯维克和曾设计东方艺术中心的保罗·安德鲁。这一老一少两位外国建筑师用自己的方式参与上海的建设,如同一面镜子,人们通过其设计的项目认识他们,而他们也通过设计的过程,观察上海。

托马斯·赫斯维克
现任英国皇家建筑师协会荣誉会员、皇家艺术学院高级会员,并于2004年获得了“皇家工业设计”勋章。他因设计了2010年上海世博会英国馆一举成名,之后又设计了2012年伦敦奥运会火炬塔和伦敦新红色双层巴士,目前作为主创设计师设计上海的外滩金融中心。

保罗·安德鲁
曾获得法国荣誉勋章、国家功勋勋章、法国艺术院院士。设计多个飞机场包括巴黎戴高乐机场,其与中国的合作也从设计上海浦东机场起步。他为中国人所熟知的设计作品还有上海东方艺术中心和中国国家大剧院。
把种子种入圣殿
在接手2010上海世博会英国馆设计之前,托马斯·赫斯维克并未意识到,上海这座城市会改变他的人生。
在此之前,他只是一个没有接受过建筑专业训练、学习过三维设计,满脑子奇思妙想的普通英国青年。因为不喜欢替别人打工,他大学毕业后就在自己家里设立了工作室。没有客户来的时候,他就在饭桌上吃饭,有人上门的时候,他就赶紧清理桌子整理出办公区域。按照现在中国青年所熟悉的话说,这是个大学生创业的项目。那个时候,他拥有的最大财富,就是时间和闯劲。
正是这个如同大学生创业团队一样简寒的队伍,最终以“一张打开的礼物包装纸”和“种子圣殿”的构思,一举打败了许多知名设计团队,赢得了2010年上海世博会英国馆的设计。为此,托马斯去了“基尤千年种子银行”,这里是世界目前最大的种子银行收集地所在。其中,一位工作人员指着一个小小植物说,这是由500年前的种子发芽长出来的。种子是在一个皮质的钱包里找到的。钱包主人是一个水手,他带着这颗种子漂洋过海去了许多地方,不知道这颗种子如何进入钱包又有过怎样的经历。但当它一旦安定下来,就会发芽。
受此启发,托马斯最终选择把种子装入英国馆的亚克力长杆,细长的杆子长达7.5米,一米多露在室外。每根杆子里都有三四颗种子。杆子本身是优良的光导体,白天光线通过杆子传入室内,夜晚室内亮光也通过杆子传递到室外。杆子随风抖动,里面安静地睡着种子,如同琥珀一般。托马斯由此营造了一个开放性的空间,用带有大自然无限潜力的种子,激发了参观者的无限讨论,也为他自己带来名誉。
如今,他从业迄今为止规模最大的建筑项目也将在上海展开。上海黄浦江畔42万平方米的外滩金融中心BFC设计方案已经公布。相比当年画下“种子圣殿”,此刻托马斯对中国已经不再陌生。他希望这一即将留在上海最重要河边的作品“必须既是摩登的,又能体现中国传统文化精髓的一些特质”。
“我们以‘外来者’的眼光审视中国文化,吸取不同城市的灵魂精髓,并进行创意表达。”托马斯说,“我一向认为建筑必须符合特定地理环境和人文特色,所以在上海的作品受到了‘中国梦’的启发:不是简单复制世界某个区域的其他建筑,而是探寻新的方式与中国杰出的建筑和景观遗产结合起来。”
在上海留下幸福回忆
相比年轻气盛的托马斯,77岁的法国建筑师保罗·安德鲁到了安定的年纪。自从22岁投身这一领域,他已经作为建筑师工作了55年了。
他因为花费十年设计了中国的国家大剧院,而被这个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所记住。不管大家对“巨蛋”如何评价,保罗都在中国的建筑界赢得了一席之地。
在为上海带来一座机场和一座艺术中心之后,此番上海之行,他仅仅带来一本新书《保罗·安德鲁建筑回忆录》,书中记录了他在法国、中国和世界各地设计和建造的建筑过程的随笔与思考。
文中穿插了大量设计草图,包括他第一次提到,正是在上海设计东方艺术中心,帮助他孕育了在中国最知名的建筑——国家大剧院的诞生。
15年前他在构思国家大剧院的同时,为上海设计东方艺术中心画草图。东方艺术中心最初的草图中是混沌的方块里几个胚胎形状的圆形,到了后期则是清晰的“蝴蝶兰”形状。外立面由五个双重内曲表面构成,如同他为国家大剧院设计的“巨蛋”形状一样,东方艺术中心没有保罗所憎恶的“糟糕的”立面。在文中,他也透露,正是在为东方艺术中心画了第一套草图后,他才决定了国家大剧院的地板、栏杆、门、座椅和其他许多细节。
“在一个同样的范畴内做其他事,换种方法来、换个脑筋来看国家大剧院既定的决策,让我能够更好地工作。正是因为如此,东方艺术中心虽然和其他项目一样困难重重,充满限制,但是却给我留下了一个幸福项目的回忆。”保罗说,和不同文化打交道的过程,就是学习和激发灵感的过程。
“而上海,始终就是那个最能激发人思维活跃度的城市。”保罗说。
设计理念
前卫的标准是什么呢?标新立异的定义又是什么呢?一个建筑设计是否好,不在于形式上是否够新奇,而在于是否能让人感受到爱与情感。随着城市的发展、空间的扩张以及人情的淡漠,大家更希望通过空间设计感受到尊严、重拾舒适与温情。
对话
一个建筑设计好不好,不在于形式上的新奇
Q:中国一度出现一种现象,即一些地标性建筑招投标中,外国建筑师所设计的前卫作品更容易中标。但现在越来越多的国人开始反感“奇奇怪怪的建筑”,更担心中国的土地成为“外国建筑师的试验田”,你们如何看待这种想法的转变?
托马斯·赫斯维克:作为建筑师,其天性就是进行艺术的创作、去尽可能追求表现形式的多样性、去探索造型空间的无限可能性。当然,我们反对去进行哗众取宠的设计,但从某种程度上说追求前卫不是设计师的失职,而恰恰是设计师的天性。至于最后选择怎样的设计,那是业主的权利。
我一直希望人们把我看成一个设计师而不是建筑师,我在曼彻斯特工业专科大学与伦敦皇家艺术学院是学习三维设计出身的。在学院的教育中,我们被要求用木头、钢铁、、塑料等材料去做设计,我相信人们对创意感兴趣,所以我工作的重点一直是对于我们周围的这个世界提出新想法。因为建筑也是一种发明。
前卫的标准是什么呢?标新立异的定义又是什么呢?在我看来,一个建筑设计是否好,不在于形式上是否够新奇,而在于是否能让人感受到爱与情感。我想,随着城市的发展、空间的扩张以及人情的淡漠,大家更希望通过空间设计感受到尊严、重拾舒适与温情。
保罗·安德鲁:当然,对毫无美感又没有用处的建筑的批评是对的,但这与设计师的审美和能力有关,而与设计师的国籍无关。中国的确是当下一个建筑设计师所梦寐以求的最好的地方。外国建筑师也的确能在中国实现许多自己不能在本国实现的作品。这倒不是因为中国是试验场,而是因为在外国建筑师的本国,城市几乎已经被填满了。巴黎、纽约、伦敦的城市建设已经完成了,而中国还在发展着。50年前,即便在中国的大城市里也缺乏飞机场和高速公路,人们也不需要大剧院和会议中心。但现在,飞速发展的中国需要这些。我也能够感受到,中国希望通过建筑来让世界看到自己的自豪。
好的建筑,应该能呈现一个时代的精神
Q:你会如何评价一个新建筑设计的好坏?
托马斯·赫斯维克:参加2010年上海世博会英国馆的甄选时,我的团队从47个团队中脱颖而出,我们设计的作品成为候选的6个复试作品之一。
一开始,英国政府非常担心我们所呈现的这个不包含任何传统英伦元素的英国馆过于标新立异,不能让观众接受,会被说是“看不懂”的。而在上海莫干山路的画廊里,英国驻沪总领事馆为最终进入复试的6项作品举行了展览,我们的“种子圣殿”深受欢迎。事实证明,这个最终由6万根发光触须组成的圆角立方体建筑“种子圣殿”,成为当届世博会最受欢迎的国家馆之一。后来这些装有包含着希望和美好寓意的种子的发光亚克力杆作为礼物,它们中的大多数都留在了上海,进入许多家庭和办公室,成为这个城市的一部分。
通过这一次的经历,我深受启发:英国在人们惯性思维中的固有形象是可以改变的,中国人也善于接受新兴事物。
不断发展中的全新的城市,需要新的形象来向世界展示自信,这不是坏事。我想,最终评价一个建筑设计的好坏,不是看它能不能“被看懂”,而是看能否通过这个设计,让人与人相遇。
保罗·安德鲁:我在设计国家大剧院时,许多中国媒体提出我没有考虑中国传统的元素,人们戏谑称之为“巨蛋”,当时的批评氛围甚至有些敌意。但一个圆的建筑在方形的水面上,没有立面、孑然一身,如同岛屿,不就是中国人说的“天圆地方”?穿过通道进入演出厅的过程犹如仪式,不正是中国元素的一种体现?
作为一个法国人,我的确不能如中国人那样说出中国皇朝更迭的顺序,也不能说出每一种龙代表什么含义,但这不代表我对中国文化没有敬畏。
从当初大家讨厌“巨蛋”,到如今人们开始喜爱和接受“巨蛋”,一些外地游客去时会特意去看看国家大剧院并与之合影,我想这很说明问题。
中国人都对生活充满信心,没有一个国度的人像这里的人一样雄心万丈。我想国家大剧院最终会被称为“非常中国”的建筑,因为它忠实记录了当下中国希望向世界表达的声音。
新颖的东西总是令人不安。但有一天,当你在未来回头看时也许就会承认,“巨蛋”和长安街上的其他建筑一起,分别记录了中国不同的时代。当下中国正在求新求变,好的建筑应该能呈现一个时代的精神。
不管规划多么宏大,人的尺度并没有发生改变
Q:和中国的客户打交道是一种怎样的体验?
托马斯·赫斯维克:中国现在已经是我的热情的源泉之地。因为中国的客户非常野心勃勃,他们总是那么充满期待地看着我,希望我像一个魔术师一样,能瞬间展现惊人的戏法,而且中国的客户也非常迷恋速度,希望有立竿见影的收获。但是一件好的设计作品,也是需要时间和耐心的。我有时候必须说服我的客户学会“等待火候”。
保罗·安德鲁:在过去的十几年里,我有幸和中国一些地方官员见面。我发现有些官员会向我提出一个共同的要求——“来给我们设计一个标志性建筑!”
好吧,作为建筑师,我理解客户提出需要一幢美丽的建筑、需要一幢舒适的建筑,但请问,什么是标志性建筑?我不太明白,为什么需要一个标志性建筑,对中国有些地方的官员来说,显得那么迫切?
Q:与中国客户合作多次之后,您作为一个旁观者和参与者,会如何向别人介绍你们眼中的中国城市建筑?
托马斯·赫斯维克:我在世界各地工作,这几年的经历告诉我,没有一个地方像中国一样,对外国的事物有着惊人的兴趣,也没有一个地方像中国一样,每天都处于变化之中。
我来上海已经很多次,但每次我来都会有新的冲击。因为我每一次来,都会看到一些之前我没有看到的建筑出现,也会看到一些我上次来还看到的建筑消失。有时候我觉得一个当代中国人一生获得的经验,可能是其他国家的人三四辈子经历的浓缩。
这对设计师来说是好事,我能够一直从变化中吸收养分、产生新的想法。因为变化是创新的基础和改变的动力。我略为担心的是,有时候步伐迈得太快了,就会忽视城市中很多小细节。现在,几乎每个地方都把精力放在做宏大的规划上,非常大的街道、非常高的楼,但是不管规划多么宏大,高楼多么摩天,有一个事实是,人的尺度并没有发生改变。人和人之间的需求,人的心灵所需要的空间,仍然和千年以前一样。
比如我留意到,上海也有些旧的建筑群落在消失。这些建筑也许在功能上不能和新的公共建筑相比,但旧的街道拥有更适合人行的尺度,老房子在材质和装饰细节上非常讲究和丰富。我关注这些细节,因为正是这些细节使得一个城市和其他城市的风貌不同。
如同纽约不是伦敦、巴塞罗那不同于巴黎一样,世界上了不起的城市都应该有自己的特点,上海应该有自己的特点。保持这种特点需要对自己的城市拥有自信,而这些自信,应该来自于对细节的关注,对人的尺度、人的感受的把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