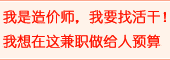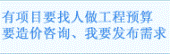Tulips Chen
冯明:中国的“消极城市化”阶段已经开始
时间:2016-07-16 01:03来源: 作者: 点击:次

从某种意义上讲,居民城市化才是城市化真正的应有之意,也是当前抵御经济增速下行压力、优化宏观消费储蓄结构的一把钥匙。
改革开放之后,中国城市化进程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劳动力城市化”,第二阶段是“居民城市化”,第三阶段是“消极城市化”。尽管中国目前仍处在第二阶段,但在部分地区消极城市化的挑战已经比较突出,亟需加强研究应对。
“劳动力城市化”阶段的典型特征是:在外向型制造业、建筑业等劳动力密集型产业的蓬勃发展下,数以亿计的农村劳动力背井离乡,到城市寻求工作机会。与此同时,这个群体的家庭、社会关系、福利保障仍然留在农村,他们在城市工作赚的钱除了少数用于吃饭、住宿等基本生活开支外,大部分仍反流到农村,用于支持家庭生活、建造房屋或者储蓄。直到近年,农民工在城市购置房产才开始流行并为政策所倡导,而且多数农民工选择在其户籍地所属县城购房,而非其打工所在的城市购房。由此产生了夫妻长期异地分居、留守儿童、留守老人等系统性社会现象;并构成内需不足、宏观经济储蓄率上升等结构性问题的根源所在。
“劳动力城市化”在统计数字上的表现是:一方面,“劳动力城市化率”或者“常住人口城市化率”的显著提高;但另一方面,“户籍人口城市化率”或“家庭城市化率”提升的步伐则要慢得多。根据《2015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截至2015年末,全国内地总人口137462万人,其中城镇常住人口77116万人,乡村常住人口60346万人,“常住人口城市化率”已经达到56.1%。但是,“户籍人口城市化率”却只有35%。两者之间存在20%的缺口。
“居民城市化”阶段的主要任务就是要让在上一阶段转移到城市的农村劳动力真正成为城市居民。
居民城市化比劳动力城市化要复杂得多———后者仅仅是农民工卷着铺盖到城市打工、出卖劳动;除了基本的生活之外,与城市很少发生交集:大多数农民工住的是宿舍、公棚或者地下室,吃的是集体食堂或者工地的灶,基本不进商场,不去电影院,不享受城市福利体系,不参与城市公共活动,家人仍居住在农村,孩子留在农村上学(或者有极少的农民工子女在城市郊区上专门的农民工子女学校)。从某种意义上讲,居民城市化才是城市化真正的应有之意,也是当前抵御经济增速下行压力、优化宏观消费储蓄结构的一把钥匙。
我们可以将城市化过程简单地比作“三级火箭”。在第一阶段,“劳动力城市化”通常是在城市“拉力”和农村“推力”的共同作用下由市场自发完成的。而当城市化进入第二阶段之后,市场化力量大大衰减,就必须通过深化改革、破除制度障碍来助推第二级火箭,补足户籍城市化率与常住人口城市化率之间的20%缺口,实现由劳动力城市化到居民城市化的升级。
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和中央农村工作会议明确提出了“三个1亿人”的目标———到2020年,要解决约1亿进城常住的农业转移人口落户城镇,约1亿人口的城镇棚户区和城中村改造,约1亿人口在中西部地区的城镇化。与之相配合的,有三项工作尤为重要:一是加快户籍制度改革,消除阻碍农村居民市民化的制度藩篱。二是在产业结构方面,要防止中低端制造业过早流出中国。只有当有了稳定的工作和持续的收入来源,农民工才可能在城市留下来,成为真正的市民。三是引导和规范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让农民除了劳动收入之外增加财产性收入来源。这既能为城市化提供推力,同时也是农业规模化和现代化的必由之路。
消极城市化是指,由于农村老龄人口自然消亡所引起的城市人口占比增加。换句话说,劳动力城市化和居民城市化都有实实在在的人口城乡流动为基础;而在消极城市化阶段,城市化率的提升并不以真实的城乡人口迁移为基础,而仅仅是分母中农村人口绝对数量的减少带来的被动提升。
严格地讲,中国正处于逐渐进入城市化第二阶段和第三阶段的叠加期,“居民城市化”仍是主要特征,但“消极城市化”阶段也已经开始。特别是在某些特定地区,消极城市化带来的挑战已经迫在眉睫。
消极城市化不仅涉及始终居住在农村的老年人,还包括一个特殊的人群———老龄返乡农民工。他们是农村户籍人口,年轻时期到城市工作,但未获得市民身份,也未能在城市购置房产,因而失去劳动能力之后不得不再次回到农村生活、养老。根据《2015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50岁以上农民工所占比重为17.9%,大约是五千万人。这不是一个小数目。
可以预见的是,逐渐失去劳动能力的老龄农民以及老龄返乡农民工由于缺乏收入来源和社会保障,同时与互联网等科学技术和现代生活潮流渐行渐远,在未来二三十年之内将成为中国社会最弱势的群体,甚至会处于被边缘化的地位。能否及时理顺农村土地经营权流转制度让农村老年人在失去劳动能力的同时获得财产性收入,并建立起相应的养老、医疗等社会保障体系,是城市化第二、三阶段的关键任务,也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最大的挑战和考验。这既需要政府的改革创新,也需要家庭、企业和全社会的协力配合。
为了应对“消极城市化”带来的考验,除了上文提到的社会保障体系建设和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之外,乡村社会治理体系的改革创新也成为必然要求。“皇叔不下县”是中国传统社会政权组织结构中长期坚持的一项原则;但这一原则显然已经无法适应现代社会的需求。特别是在消极城市化阶段,农村人口老龄化要求政府必须在乡村承担更多的责任,包括提供公共服务和参与社会治理。
这就势必牵扯到乡村行政区划的调整。乡村行政区划调整是提高基层行政效率的必然要求,一方面能起到相对缩减社会治理成本的作用,另一方面也有利于合理配置人力物力,优化基层政府服务职能。
中国在1992年、2001年、2005年和2011年经历了四轮大幅度的撤乡并镇工作。乡镇级行政区划的数目已经通过裁撤合并的方式由1984年最高点的10.6万个缩减了超过一半。其中,乡的个数由8.5万个减少了1.2万个,镇的个数增加到了2万个。另外,城市扩围引致街道办事处的个数增加至7696个。
行政村虽然不是一级政府,但作为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事实上承担着大量的乡村社会管理工作,尤其是在对接执行、分配和监督层面。行政村的数量由2000年的73.2万个减少到2014年底的58.5万个,减少了五分之一。平均每年通过撤并减少约1万个行政村。
随着农村空心化和人口老龄化,预计未来撤乡并镇、乡镇改街道办事处、行政村合并的进程仍会持续。
另外,贯穿城市化三阶段的一条主线是农业的转型升级。农业转型升级是解决好农民问题和农村问题的根本所在,是解决好“三农”问题的提纲挈领之处。在城市化的第二阶段和第三阶段,依然如此。而农业生产效率的提高只能来自于两条路径:一是细化专业分工,二是加强一二三产业融合。
“细化专业分工”是指,越来越多的生产环节从传统的农业生产中独立出来,成为专业化的细分工种。最早的农业生产是一体化的,每家每户都从事从育种到销售的全产业链工序。而随着专业分工的细化,育种、化肥制造、销售等环节逐渐被剥离出来,今后诸如播种、温光湿控、农产品物流、品牌建设、融资、农业保险、甚至施肥、喷药等环节都可能会独立出来,由专业化企业来经营。
“加强一二三产业融合”是指,农业与制造业和服务业之间的交集将越来越大,界限在未来将越来越模糊,一种农产品从农田到餐桌的过程将依赖于隶属于一、二、三产业的多个经营主体之间的相互配合。未来的农林牧副产业将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一次产业”,而将成为“六次产业”。细化专业分工和一二三产业融合这两条路径蕴藏着大量投资和创业机会,都建立在规模化的基础之上。当然,必须强调的是,农业规模化应当与城市化进程相协调。既不能揠苗助长,也不能畏首不前。过快容易带来不稳定因素,可能引发社会动荡;过慢则会限制现代农业进步和城市化进程。
(作者系中国社科院财经战略研究院、省敦煌市转渠口镇党委副书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