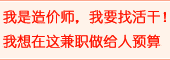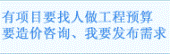Tulips Chen
周源:建筑向死而生
时间:2015-11-24 15:15来源: 作者: 点击:次

德国比伯拉赫应用技术大学 周源
80后建筑师周源在德国深造,读他的有关采访,你可以了解到当代德国建筑教育与中国建筑教育的截然不同。周源说:“在德国大学,本科生是可以做到理解建筑细构,并且能自行进行细构设计的。而到了研究生,在构思方案的时候就几乎可以把整个建筑用实际技术在脑子里完整地搭建一遍了(人肉BIM)。正是这样的教学侧重决定了德国在建筑技术和施工上的先进。而从德国建筑师的角度上看,99%的中国建筑毫无细构可言。”
同时,我很欣赏他在学习中不断比较文化差异、扬弃和选择性地吸取知识营养的过程。周源坚持找寻适合自己的发展路子,不但写下了自己观点鲜明的评论,而且坚持“自由建筑”的创作,我相信他将来会有所成就。
Q:看了你的简历,是个热爱旅行的建筑师,请谈谈你认为从古至今最精彩的建筑在哪里?中国建筑在世界建筑史中的独特性是什么?
周源:和很多喜欢建筑的人不同,我对于欧洲古典时代的建筑没有什么特别的好感,甚至可以说有些反感。我讨厌巴洛克之后的繁复装饰,讨厌新古典主义和折衷主义的不知所云。乌尔姆和科隆的大教堂除了高大复杂并没有什么特别之处,甚至罗马城与帕特农神庙的废墟也没什么能让我“潸然泪下”的地方。在我看来,欧洲古典时代的建筑只不过是一些权力阶级精巧的玩物,布满符号和无用的装饰,和自鸣钟、首饰盒没什么区别。直到现代主义兴起,建筑才有了现代意义上的“设计”。自此开始,建筑才变成了真正动人的艺术,因为它开始充满了澎湃的思想、激情与人文关怀,建筑开始属于全世界,属于每一个人。从法国,德国,美国然后是全世界,新的建筑与新的思想每天都在不停地被创造出来,互相碰撞,激发出更大的火花。这是最精彩的时代,就像站在反应堆的中心参观一场剧烈的核聚变,或者是一次广场上的即兴诗会。所以在我看来,最精彩的建筑未必有一个明确的地理坐标,但它在历史上的位置却是清晰的,那就是现在。这是最精彩的时代。
但关于古典建筑,有一个例外那就是中国古建筑——虽然同样布满符号和装饰,但出于文化和历史认同感,我无法回避中国古建筑的魅力。在德国学习建筑史,几乎永远都是大教堂,大剧院等等,对于泛中华文化圈的建筑体系总过不会提到超过两句话,且配的图片也无非是一个清晚期的亭,再加上一个太和殿的重檐庑殿顶。好像对于西方人来说,中国的建筑是遥远且不重要的。所以他们只能把古希腊柱式和帕拉迪奥母题这样简单的东西翻来覆去的讲。其实比起古罗马-希腊体系的建筑学,中国的建筑体系在材料、结构、哲学和栖居方式等等方面发展得要更成熟一些。我们有完整的木结构发展图谱,有诸如应县木塔这样的工程杰作,有寄情山水的园林,还有各地不同形态的民居聚落。然而建筑始终是根植在社会土壤之上的。中国过度成熟和森严的中央集权体制一方面制约了建筑本身形态的发展,另一方面也制约了城市形态的发展。这在近现代进入公民社会之后产生了明显的不适应,大概也是中国传统建筑消亡的原因之一。因此在现在,在这个中国的文艺复兴时期,如何继承祖先的经验和传统是一个非常值得探讨的问题。在这个问题上,我对那些仿古建筑持极端的批判态度。我们不需要假古董,不需要在外部形式上搞什么所谓的复古,而是需要思考和探索古典的经验和精神,在历史中挖掘值得借鉴和继承的财富。毕竟建筑所根植的另一种土壤则是哲学,而中国古典建筑体系之于西方建筑的不同从根本上说是哲学体系的不同。在我看来,与那种非黑即白的西方哲学体系的根本区别在于中国人讲究的是“调和”。这种思考方式渗透了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从厨艺到中医药,从书画艺术到武术。“调和”造就了中国古典建筑的独特个性,也是一个最值得我们当代中国建筑师深入思考的命题。
Q:我很久以前就开始关注你的网站“建筑师之死” 了,每次路过这里,都会驻足看看。老实说,收获挺大。为何给网站起这个名字?设立这个网站的初衷和目的是什么?
周源:“建筑师之死”这个网站缘起于我对这个专业将要入门还未入之时,却隐隐感觉到我所接触到的中国建筑设计的水平普遍与欧洲的设计存在着不小的差距——既有观念上的,也有技术上的(当然这很大程度上也是出于自己当时见识太少。其实中国有很多优秀的建筑师那时都处在爆发的前夜)。所以我决定做一个网站,翻译一些德语和英语建筑杂志的内容,帮助国内的同行们了解欧洲建筑师们现在在做什么,在想什么,同时也是帮自己更好的理解建筑设计的奥义。但很快我就发现单纯的译稿既不能满足读者,也不能满足自己。所以我开始自己写评论,整理自己的一些想法,希望与更多的人探讨,也可以结识更多志同道合者。好在我从小就喜欢写作,所以自信也练得一手好文章。在中文网络中,介绍外国建筑设计和写建筑评论的网站多如恒河沙数,但我自信自己的评论不乏独到的想法与最好的可读性。这也许是“建筑师之死”与其他网站最大的不同。一开始的文章是偏激且片面的,甚至让自己都不忍回看。但细数历程,我也能感到自己在网站的写作中一步一步走向成熟,读者也渐渐多了起来。
“建筑师之死”这个名字其实一开始并没有什么深意,只是在熬夜做设计之后的极度的疲劳里发出的一些牢骚——不过这个名字听起来可能让人印象深刻,虽然也有很多人指出名字不积极,“很不好”。但我想这世界上有那么多取着光辉万丈的好名字却在做着庸庸碌碌事情的人,我不想和他们混到一起。就如同有那么多人在用着让人看不懂的不负责任的华丽辞藻描述着建筑学的神圣和深奥,我却在用最普通的语言解释着建筑学中那些别人不屑于谈的小事一样。从这个角度上说,“建筑师之死”这个名字其实代表着一种解构主义。我就是要拆掉那些不怀好意的人给建筑学搭起的高大神坛,让更多人能理解建筑学的魅力和我们建筑师正在做的事情。如果建筑师必须穿着黑西装,高昂着头颅维持着教士一般的威严的话,那建筑师就必须死。
Q:很喜欢你今年参加德国建筑师联盟的雨果-海灵新人奖的竞赛作品,在《第三名没有奖杯》这篇文章分析的很透彻,评论也很真诚。我想推荐给每筑建文的粉丝们看看。看得出,你希望通过设计理念上对使用者和环境的关怀,塑造建筑的形体,而且它是有机的和有特色的。你的这个设计有中心思想吗?王澍的造园理论对你的影响又是什么?
周源:在“小山幼儿园与成教中心”那个设计里,我的中心思想就是要改善地区环境,同时给孩子和家长们一个丰富的小世界——当然把这个作为中心思想似乎显得单薄,实际上我当时更多的是在凭着直觉实践一些手法。后来想了很久,脑子里逐渐出现一个词“自由建筑”。什么是“自由建筑”呢?这样的建筑就像是一株植物,一棵西兰花或者。我尽量不给它设定一个整体的形态,而只是设定它生长的逻辑,就如同设定植物的基因,然后让他们自由生长,自发地回应环境和功能。我认为这样的设计逻辑会产生一个如同植物一样丰富且灵活的建筑体,一个根植于环境,改变着环境,却又有自己独特个性的建筑体,而不是一个突兀的置入物。在面对一些不带有强烈符号性的公共建筑设计上,这样的设计逻辑也许会产生一些很有趣的东西。当然,“自由建筑”这个概念在我脑子里仅仅只是一个雏形。也许十年二十年之后,当我有了更多实践经验时,会以这个题目出一本书也说不定。
而我认为“自由建筑”这个概念很大程度上来自于我对王澍造园式建筑逻辑的一些感想。我把宁波博物馆和瓦山旅舍的构成分解为一个又一个的“Place(中文似乎叫做“场域”,但我不喜欢这个词的拿腔拿调)”,然后把这些Places用超越平面的三维交通曲折地连接起来。形成一个并不高效,也不严肃的闲适的建筑空间,或者叫做“游览空间”。建筑空间不一定非要高效紧凑,也不一定非要处处实用。在自由生长的过程中一定会产生很多非理性的甚至无意义的地方,但这也是趣味的来源。所以“自由建筑”一定是有趣的建筑。
Q:在德国的建筑学院学习,你觉得收获的是什么?大家一般会认为德国设计讲求精致的细部,对建筑夸张的形体创新不感兴趣。你觉得是这样吗?
周源:在本科阶段最让我恐惧的内容,以及让我决定留在HBC读硕士的动机,就是1:25的细构设计了。很多国内的老师都不相信,在德国大学,至少是在我们HBC,本科生是可以做到理解建筑细构,并且能自行进行细构设计的。而到了研究生,在构思方案的时候就几乎可以把整个建筑用实际技术在脑子里完整地搭建一遍了(人肉BIM)。正是这样的教学侧重决定了德国在建筑技术和施工上的先进。而从德国建筑师的角度上看,99%的中国建筑毫无细构可言。
但在技术之外的部分,德国人的确表现出了严重的漠视。我曾经不止一次问德国同行:为什么总是方盒子,为什么总是不等宽窗子组成的外立面,或者又是刻意不做方盒子而弄出的莫名其妙的无理造型?没人能回答,他们大多只是耸肩。大概德国人本来就是一个无趣的民族。
德国建筑师的这个特点与喜欢玩弄概念、几乎不考虑现实的英国大学完全不同。英国的大学生喜欢弄一些晦涩、毫无实际意义的概念设计,似乎被后现代艺术毒害了脑子;而德国人则能弄出一些实实在在的高效能方盒子,无趣地矗立在大地上。此二者皆不可饶恕。
当然这也并不绝对。德国一样有蓝天组,一样有斯图加特大学的参数化凉亭;而英国也有托梅-奥尼尔那样踏实的建筑师。一概而论,往往失于偏颇。
Q:谈谈你最喜欢的建筑师,或者最难忘的一段经历。
周源:本科毕业之后我已感到心力交瘁,于是回国呆了一年,休养生息,整理思路。有一次去舟山参加一个聚会,在返回的途中绕道去了宁波和杭州。一开始只是想看看天一阁,看看西湖,但在火车上却突然想到了一个名字:王澍。于是我就带着好奇心走进了宁波博物馆,接着是五散房,宁波美术馆,杭州宋街与中国美院象山校区。然后我沉默着回去了。接下来的很多天里,我都在混乱的思考和震撼中无法自拔。从没有哪一个建筑师的作品给我带来如此大的颠覆和共鸣。之前从杂志和网络上读到一些关于王澍充满溢美的描述往往让我感到费解,而身临其境却让我恍然大悟,有如醍醐灌顶。于是我整理了很多页笔记,最终写成了一篇名为《寻找王澍的旅行》的文章,发布在“建筑师之死”上。
——“经验告诉我:要想透彻理解一个建筑,光从纸面和照片上是很难得到全部信息的。因为纸面信息通常是理性且直观,有时候甚至是片面的。而建筑(此仅指经过设计的建筑,下同)带给参观者的第一感受却是情感上的冲击,或者说是将受众带入一种气氛,一个建筑师的精神世界。有很多东西是照片无法表达的,比如环境,空间感受,或者建筑师对于使用者在细节上的人文关怀。再加上很多时候摄影师更关注于构图和一些他自己认为新鲜有趣的角度,于是建筑设计在摄影作品中呈现的样子总是被曲解。所以通过网络和传统媒体传播最广的往往是那些看起来很抓人眼球的建筑,但那不是建筑的全部,更不是建筑设计的全部。须知:要透彻理解一个建筑,没有比身临其境更好的办法。”
——“在文化这件事情上,王澍的设计手法显得比较激进,甚至有些不顾公众的接受能力,以至于总要用实际语言向甲方和公众解释他的设计才能平息争论(在更大范围内甚至根本没法平息)。但不是每个人都能有辩解的机会,也不是每个人都会有一个支持有力的后台。如果你也学着王澍那样做一个乍一看上去灰头土脸的设计,那么不管你在设计内部蕴含了多少更深层次的文化寓意,你的设计也多半会被一句话毙掉。王澍的建筑语言、设计手法和经历都是不可复制的,因为他的做法不具备普遍可操作性。这并不是说他的设计不实用,恰恰相反,宁波和杭州当地人对于王澍的设计的接受程度出奇地高,因为他们会对王澍的设计产生文化上的共鸣。从这一点上说王澍是非常成功的。
所以我们换句话说,王澍迄今为止比较成熟的设计,从宁波美术馆到象山校园三期,都带有相当程度的实验性。因为王澍自己也不确定为了回归传统文化应该采用什么样的具体解决方案。用他自己的话说,是“这才刚开始,后面还有很长的路”。
这个新的方法论给我带来了一系列问题:建筑一定要在所有细节上百分之百正确和实用吗?是否可以有一些非理性、非实用主义的部分,借此舒缓空间紧张感带给人们的精神压力,从而把建筑变成一个更感性的空间呢?这样做一定就浪费面积和成本,降低实用性,而且得不偿失吗?建筑可以成为容纳社会活动之上、也能容纳精神的场所吗?
这些问题让我开始从根源上反思自己所接受的所有建筑学教育。在德国的大学中,建筑设计似乎只有对与错之分,而根本没有美与丑的区别。至多,只是“有趣”的设计。我突然觉得这一切都太实用主义了,德国人把建筑看成了一套机器。它们运转精良,但却空洞无味。而我在此间呆的太久,已经离我自己的文化太远了。”
是的,我们只是建筑师,很多时候我们说了不算。但在“利用建筑作为开端重塑社会文化价值观”的大目标面前,总有人会选择忠于理想。这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甚至有时候会逼得人忍辱偷生。甲方需要高端大气上档次,你该怎么跟人解释你却要为了保留文化地位而刻意缩小建筑尺度?也许你需要一副好口才,或者仅仅只是在设计的细节上践行自己的某些想法。当这想法起作用的时候,总会有人看到文化带来的好处。当有无数人都在做这件事时,便会像无数小溪汇聚成江河,奔向大海;或者说形成一种时代性的思潮。当下的中国,如果要向传统回归,需要大量的实验建筑或者建筑的实验。这不是王澍一个人的事情。
而如何“继承”,王澍在设计中提出了他的思考。从已建成的项目中看,他的思路是成功的——不管是当地民众的普遍看法,还是我自己的亲身体会,都在王澍那看似“不合理”的设计中找到了前所未有的共鸣,这其中既有传统手工材料纹理和技法的功劳,也有那看似随意实则处处透着自然哲学的平面布置的功劳,尤其是在瓦山旅社中沿着弯曲的徒步道从一楼一直走到楼顶瓦片上的体会,让我惊讶得无以言表。我从来不知道可以这样理解建筑,把建筑弄成一座可以漫步其中的园林,利用徒步道连接所有平面空间甚至瓦片屋顶之上的空间,而让所有功能空间如同园林中的假山凉亭一样随意放置其间。从我们接受的传统方法论看,这是完全错误的,是存在着大量浪费和“不正确”的设计。但在瓦山旅社中流连忘返的几个小时让我明白,错的不是王澍,而是我们对建筑的理解方式。
更重要的是,王澍的设计证明他的思路是可实现的,至少是在某些地方可实现或可局部实现的。这与那些玩弄虚无概念的建筑师有着本质上的区别。更何况王澍已经证明了他的设计手法,所产生的效费比远远高于那些亮晶晶的搭成的现代主义建筑。……
当然,当时的想法还很不成熟,缺少深度。但这次短暂的旅行却给我的设计思路造成了深远的影响。我开始认真思考诸如我们到底为什么而设计这样根本又宏大的命题,并试着探索将王澍带给我的那些关于传统文化与哲学的启发实际应用到手头的设计上去。正如我之前所说,“自由建筑”,大概就是这影响的一个小成果。
据一个朋友说,他把《寻找王澍的旅行》这篇文章发给了王澍老师的秘书。这让我很惭愧,因为这样一些稚嫩的想法未必能入得了前辈的眼,也不能代表我后来更进一步的想法。又听朋友说,王澍老师看了文章,并说“有机会可以聊聊”。只是随口一句,却给我带来了莫大的鼓励。
像王澍老师这样的前辈们为我们这一代人打开了一扇门。这扇门的背后,将会是一个时代。
Q:80后青年建筑师与70后、60后建筑师相比,你认为有什么不同?
周源:每一代人都有不太一样的价值观和思考方式,这大概是因为社会形态与获取知识的渠道变化所致——而在中国,过去的几十年里这样的变化或者说是进步尤其剧烈,所以一代一代的人也表现出了很明显的不同。虽然人类素来有先一辈人看轻后一辈人的传统,诸如我们80年代生人小时候背负的那些诸如“垮掉的一代”的忧虑,但我却始终认为每一代人都会比上一代人有进步。甚至现在90年代的一代人,往往都表现出了比我们当时更优秀的一些特质。在这个问题上我很乐观。
从一个80年代出生的建筑师的角度看,首先应该说的是我们建立在开放型社会以及后来网络时代信息爆炸之上的知识视野,是很多前辈不具备甚至无法设想的。如果说再长一辈、在青年时经历过社会剧变的一代更容易被《河殇》一类逆向民族主义扰乱心智、在很多问题上迷茫的话,那80年代出生的一批人则更自信,有底气与世界平等地交流。这不仅带来了更加国际化的视野,同时也帮助我们在更频繁的文化交流中认清自己的位置。另外,时代背景的变化,让我们这一代人自我意识更明确,更关注人性自由和解放,有更开放灵活的思想,这具体到设计上也会产生许多有趣的不同。此为其一。
其次,80年代出生的建筑师们对电脑并不恐惧。我曾在另一篇文章《手绘VS软件,软件VS软件》中论述过一个由软件解放建筑师生产力的小规模产业革命。在这篇文章里我认为,之前的建筑师们往往因为出图的困难和缓慢导致对图面过分看重,反而忽视设计本身。而大规模的软件应用之后,建筑设计发展的速度陡然加快了,因为我们被解放出了更多时间和精力,可以用来对设计进行更好的思考。另一方面,3D辅助设计让我们对建筑的理解和思考从图纸的二维平面变成了三维的,所以能更容易地做出一些前人无法设想的东西。当然,这里并不是说电脑辅助设计是80后的专利。只是这一代人用起电脑更加得心应手而已。
再次,近现代中国的建筑设计普遍水平,无论空间语言、造型、还是具体的结构、建造技术和施工水平都有落后的地方——虽然偶有大师佳作,但也是孤木难支。这和社会发展、公众普遍接受能力和审美能力、建筑成本和技术实力都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但我认为社会发展水平继续提高,以往的粗制滥造的建筑设计方式将越来越不符合时代的需求。在我们行业内部同样也存在一个淘汰落后产能的问题。而如何提高整个行业的水平,向着发达国家奋起直追,则是我们一代建筑师的责任,也是很多人今时今日正在做的事情。
当然,指数增长的日常信息交流和越来越强大的辅助设计软件也带来了一些副作用,导致很多新成长起来的建筑师过分追求建筑设计一些表面化的东西,对设计本身不够严肃。但我认为这是年轻人的通病,时间和经验会让人沉下心来。
最后要指出的是,我并不是太赞同用出生年代给人贴标签。虽然不同年代的人会有不同的特征,但具体到个人,则是千差万别——况且年代并没有一条分界线,79年出生的人与81年出生的人未必会有什么很大差别。更何况有些共性是超越时间的,那是一种类似于传统,甚至“建筑师之魂”的东西,引领我们选择这一行,并在以后的道路上行端坐正。总之,人类总是在进步的。我们强于前人,我们的后辈又会强于我们。也许偶尔有些倒退,也不过是所谓“螺旋上升”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