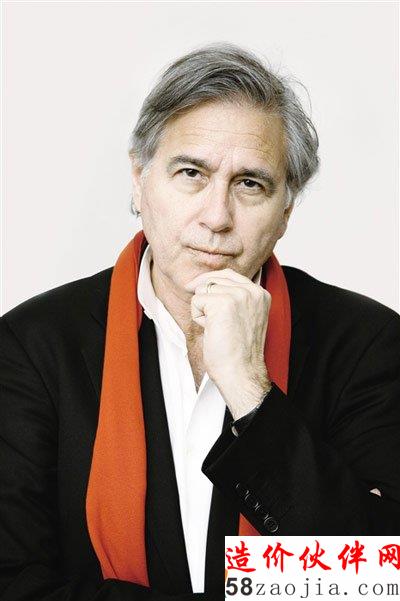
2017年将对公众开放的现代城市与工业博物馆(Tianjin Exploratorium)是伯纳德·屈米建筑事务所在中国的最新项目。伯纳德·屈米头戴安全帽,在中国建筑一众人员的陪同下穿行于尘土飞扬的工地,红色围巾在钢筋水泥间尤为醒目。然而,视察项目进程只是此次中国行的目的之一。
3月中旬,伯纳德·屈米在中国的首次大型回顾展“建筑:概念与记号”在当代艺术博物馆(PSA)开幕。此次展览围绕伯纳德·屈米作为建筑理论家、建筑师及文化领导者的多重身份,共展出近350件图纸、手稿、拼贴画、模型等珍贵资料,包括久负盛名的《曼哈顿手稿》、《乔伊斯的花园》等。
如今已年过古稀的伯纳德·屈米因2003年的798工厂改造方案而与中国结缘。当时798工厂已经逐渐被艺术家工作室、画廊和书店占领,但政府更希望把这块艺术中心改造成住宅区。
伯纳德·屈米希望能找到一种解决方法,在满足开发商经济利益的同时保护艺术区的公共性质。于是他四处走访画廊,一天又一天地在的胡同里穿街过巷。
“我习惯随身带着本子和笔,一有什么想法,马上记录下来。”伯纳德·屈米向记者描述那段实地走访的历程,“这样一直走访到5个月后,我的工作室才提出了一个比较完整的设计方案:保留地面层现有的老建筑,在其上建立一个距地面25米的高密度住宅区。798工厂改造的模型是新与旧的融合。传统与创新的结合本身就是一种艺术手法,而不单单是建筑设计。”
艺术是伯纳德·屈米的人生关键词。他不止一次表达过建筑从来不是一个独立的学科,而是与电影、文学、音乐等等互相交叉的学科。
“我曾经还想过做导演呢!不过人一辈子做好一件事就很难得了,最终我还是选择了建筑。”屈米笑着说。在《曼哈顿手稿》中,他大量运用电影中常见的蒙太奇手法,通过描述真实事件的照片、建筑平面图、剖面图等等,让空间与功能、行为与脚本这些传统建筑表现模式中所缺失的东西,得以生动地表达出来。
20世纪70年代中期,伯纳德·屈米注意到很多文学作品对空间的描述都与建筑遥相呼应,于是便根据詹姆斯·乔伊斯创作的《芬尼根守灵夜》设计了大型城市规划项目——《乔伊斯的花园》。
Q:“建筑:概念与记号”大型回顾展囊括了您职业生涯大部分的作品与理念,但展览主要由图纸、视频构成,连模型都很少,您觉得观众能通过这些很好地理解您的作品吗?
伯纳德·屈米:任何建筑,甚至任何艺术作品、任何音乐,都可以被递进地理解。当你看到一幅画或者听到一首歌时觉得喜欢,那么你获得了最表面的信息,这是第一层理解。接着你试着去解读你所喜欢的东西,试着明白作品背后的创作动机,这是第二层理解。这个展览就是按照这样的层次布置的。墙上是各种手稿和作品图,你可以一眼判断出哪一件作品吸引了你。当你在某件作品前驻足,会发现每一幅图稿的旁边不光有文字说明,还有向观众提出的问题,这是为了引发观众的进一步思考。
Q:您提出了空间与事件、向量与围合等等独有的建筑概念,您是如何在实际设计中融和这些抽象理念的?
伯纳德·屈米:人们常常忘记建筑是关于空间和时间的。人的运动是建筑的一部分。建筑无法脱离运动、事件以及发生在其中的活动而存在。因此,我认为在设计中应该把时间和空间都考虑在内。在《曼哈顿手稿》中,我就加入了人的运动和行为,虚构了一个故事,让事件可以在静态的建筑中得到体现。
围合的设计理念现在已经变得普遍,它转变或者消除了建筑门面外观以及顶部的观念,引领你去想象所有的可能。这种思维方式是我的作品的共性,它远远超越了建筑外观上的差异。人们对建筑物内部功能的要求与外部不同,双层围合因此有了用武之地。内部围合需要考虑人们对活动的需求,提供舒适的环境。外部围合主要是保护,它也可以发挥城市地标的作用。在设计江诗丹顿位于日内瓦的总部及制表厂大楼时,我就运用了双层围合的概念。一层的结构材料为穿孔钢膜,在提供保护的同时可以让光线射入,制表部门被安置在这里,工匠们享受既私密又舒适的工作环境,其他的正式空间则可以用来接待客户;另一层结构则类似外衣的内衬,只不过它的材料不是布料而是木材,其作用是保暖、隔音和透光。所有事物和员工都被容纳进了一个整体的大围合中,同时内外围合各自发挥作用,让这座建筑的内在得以表达。
Q:您反复提到建筑与其他学科的共性,并且在作品中进行实践,怎么具体理解建筑不是一个孤立的学科这一概念?
伯纳德·屈米:建筑与其他学科的共性完全可以通过类推和比较得出。比如电影通常是由一系列镜头组成,每一组镜头都会发生一系列动作,镜头与镜头之间有衔接。文学作品也是一样,一本书通常一章节一章节地联系起来。建筑同理,先是有“进门”的区域,接着是“等待”区,然后有上楼的“台阶”,我可以把建筑的每一个部分都当做一组镜头或是一个章节来看待。每两个分部之间的衔接可以是粗暴直接的,也可以是柔和顺畅的。电影里从一个镜头跳到另一个镜头,有时大开大合,有时淡入淡出。同样的手法也可以运用到建筑设计上。这样的理解让我能经常从其他学科中得到建筑的灵感。
另一个证明建筑不是孤立学科的例子是类型学的由来。建筑学领域用类型学来阐释不同类型的建筑。但类型学这一说法其实是18世纪时由自然科学家发明的。自然科学家告诉人们马、狗、羊之间的差别,告诉人们物种的概念。
建筑学家看见自然科学家绘制的图表,于是就借鉴过来,运用到了建筑学领域。换言之,知识的确是可以被分享的。
Q:距离您第一次参与中国的项目已经过去了十多年,现在回头思考中国建筑设计界过去10年的进程,您有什么想法?
伯纳德·屈米:中国建筑的变化太大了。但当我们谈论中国建筑时,并不只是关注某一个建筑师个体或单个建筑项目,而是把中国建筑的整体发展情况当做研究对象。所以与其说是建筑变化了,不如说是城市以及城市生活变了。
城市通常需要千百年慢慢演变,而过去的几十年,中国城市的进程非常快,不得不说这是个巨大的挑战。这样快速地发展非常困难,我能理解因此而产生的问题。但城市的意义不仅在于鳞次栉比的高楼,更在于它对城市居民和文化生活产生的影响。也正是基于这样一种对城市的理解,我才迷恋城市,决定做一名建筑师。我最遗憾的是现在许多城市都看上去很相似。我更希望看到每一个城市都能有独特的发展方式,城市与城市之间可以有更多差异。身为建筑设计师,我们应当对这种现象承担一定责任。 (责任编辑:建筑小白)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