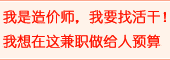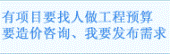Tulips Chen
矶崎新:我不介意被称为“建筑界格瓦拉”
时间:2015-05-28 05:40来源: 作者: 点击:次

日本侵华罪行馆设计师 矶崎新
人和人的相遇才是最重要的
矶崎新在日本原就以左翼人士自居,提及接手日本侵华罪行馆项目的原因,老先生絮絮叨叨地开始聊起和很多中国建筑师、艺术家的交往过程。
“从上世纪90年代起,我就开始从外围关注中国的建筑界,一次在双年展上,刘家琨、张永和等人给我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也开始和他们有所交往。”受刘家琨之邀,2003年矶崎新前往成都参观鹿野苑石刻博物馆,这座刘家琨早年的作品既融入了中国本土元素,又有现代主义风格,矶崎新觉得看到了当时中国建筑的“时代感”。
参观后,刘家琨建议,既然来了成都,不如顺便去看一看建川博物馆。位于成都大邑县的安仁古镇,是远近闻名的刘氏庄园所在地,庄园始建于明末清初,由刘文彩、刘文辉等五兄弟的公馆和刘氏老宅组成。不过矶崎新在那里找到的最初的熟悉感来自1960年代末的大型泥塑群“收租院”。曾经与矶崎新在日本有过合作的中国艺术家蔡国强,因为1996年威尼斯双年展上的作品《威尼斯收租院》奠定了他在国际上的地位,矶崎新没想到老友作品的原型就在中国内陆的这个小镇上。
在那里矶崎新见到了“野心勃勃”的、想在这里建一个博物馆群落的樊建川,当时已经有了一张规划的总体平面图,好友刘家琨和张永和也已经参与其中,分别“认领”了红色年代章钟印陈列馆以及红色年代宣传画陈列馆,之后两人也热情邀请矶崎新加入博物馆群落的建设。
“老先生说了那么多的意思是,他选择这个地方做这个项目的很大原因,是缘于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和亲近感。这不是一个专门的任务,(接下项目的想法)是在交往、观察、聊天中形成的。”矶崎新的中国合伙人、翻译胡倩解释。
矶崎新感兴趣的不只是人情。馆长樊建川向矶崎新介绍了自己丰富的藏品,从小镇上刘氏家族的历史遗物、中日战争时包括援军和盟军在内的物件,到“文革”期间的相关收藏,当然还有他想利用安仁镇的资源与自己的藏品来建造一个文化主题公园的想法。矶崎新认为,传统的博物馆大都以国家历史的宏大叙事线索来进行陈列,而这个籍籍无名却有着独特城市风貌和历史渊源的小镇,加上樊建川所收藏的中国近代历史发展中零碎的物件,呈现的是同主线不一样的历史脉络。“撇开政治感情,战争的残酷将人民卷入了无辜的死亡中,加害者与受害者永远是一对矛盾,在这里,所有的过程将得到客观的真实的展现。”他说。
这种将历史脉络和城市发展相联系的个人雄心在矶崎新看来非常独特,所以当被邀请设计日本侵华罪行馆时,他欣然答应。
“建筑要存在百年以上和它波长相同的是文化”
最近一次回安仁的时候,矶崎新对采访他的记者说,“南京大屠杀要讲够,大轰炸也要讲够。”言谈间,这位近十几年才将工作重心转移到中国的日本建筑师总让人觉得,他对中国近代史的了解和认知要远高于一般的日本民众,被问及此,他回答说,这和自己的家庭背景是分不开的。
在矶崎新的记忆里,祖父母都可以写汉字、作汉诗,家中一直浸润着浓厚的中国文化氛围。他的父亲曾留学上海,是东亚同文书院(1901年日本在上海创立的以进行“中国学”研究为专务的高等学府,现为爱知大学)的学生,接受的是亚洲主义的思想,坚信应以中日为基础,联合亚洲其他国家,平等互利,实现共荣。中日战争爆发后,他的父亲回国。
矶崎新出生在九一八事变发生的1931年,小时候,家中有着浓郁的中国文化氛围,对政治漠不关心,而这种醉心于中国的氛围也让他的家庭一度很受孤立。“比我年长10岁、20岁的人都被国家征召入伍了,很幸运我当时还是个孩子。虽然当时整个国家笼罩在帝国主义的阴霾下,但我一直受家里的熏陶,所以从小就对中国有一种亲近感。”战争结束以后,矶崎新学习建筑,接受的多是西方的一套理论,也就与中国“小别”了一阵,不过1970年代后期当日本首次派中日文化交流的学者赴中国时,他积极响应,开始重新认识中国。
以矶崎新的角度来看,1978年他来中国的时候,战争已经过去了三十多年,中日的关系十分融洽,日本不仅看到中国市场的巨大可能性,整个日本国民也相对友好,许多中国人选择去日本留学。“我记得当时有个调查数据显示,日本民众对中国的友好度超过90%。”矶崎新回忆。
然而从1980年代到1990年代末,日本经济泡沫破裂、苏联解体……整个政治环境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国家与国家间需要建立新的秩序。“中日媒体的报道可能有所差异,但从日本的报道来看,1998年江泽民访日是一个转变的契机。之后,中国就开始对日本挑明历史问题,关系持续僵化,民众也互不信任。”
身为建筑师的矶崎新在这一点上有切身的感受,他告诉记者,1998年中国国家大剧院的竞投项目一共有两轮,直到现在还会有当时的评委和他聊起说在第一轮竞投中,矶崎新的方案很受好评,“也许就是第一名呢。”据说当时还有专家联名写信争取方案,“总之在文化层面他们非常认可,我后来了解到有一些反对意见:在天安门广场上不可以有一个日本人的建筑。”
他有一些无奈,因为自己并不是以一个日本人而是建筑师的身份去设计国家大剧院,在矶崎新的心中,政治环境5到10年有一次更迭,文化100到500年有一次飞跃,而民族问题也许千年都很难变化,这些都不是相同波长的问题。“建筑是要存在百年以上的产物,和它波长相同的就是文化,所以我一直着眼于文化层面的考量。”
“我是国际人矶崎新”
矶崎新有一次参加中国的一个建筑师论坛,在介绍他的时候全场突然笑了起来,翻译说主持人介绍他为“日本建筑界的切·格瓦拉”,他表示不反对这样的说法。“在我的职业生涯中,一直是站在政府的另一边,有一定的对抗性。就像艺术家一样,应该超越现实的体制,追求新的发展。”
然而建筑要与城市发生关系,势必要与政治发生关系,矶崎新觉得建筑师是最能感受到政治变化的职业之一。“我不太希望别人介绍我的时候说我是一个日本建筑师,我是国际人矶崎新。但是不管怎样,这个身份印记会一直背负着。我也希望能够通过建川‘日本侵华罪行馆'这件作品来阐释我对政府提出的异议。”
日本侵华罪行馆的建筑面积约3500平方米,顶部设计宛如波浪,灰色外墙,入口曲折逼仄,展厅略显狭长,整个建筑采用当地的砖料与混凝土混合,呈现出历史沧桑的气息。
矶崎新可以理解樊建川的是,作为私人投资者在这么大的博物馆聚落建设中必然有资金分配先后的考量,比如2008年大地震后,汶川地震博物馆先行建造,其他的项目就整体延后。另一方面,从选材上也尽量节省成本。早年矶崎新曾放话说,这座纪念馆“我不要钱也会建”,被问及此,他笑说当然没有完全不收设计费,但是也差不多。
2015年9月3日,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纪念,建成的日本侵华罪行馆选择在这天开幕也是借着这个由头,不过这样一来,又不可避免地将人们的关注点引向了战争和历史。矶崎新觉得没什么人关心建筑本身,有客观原因,也挺正常。
“建筑的生命力有百年,我从设计之初就会考虑它的未来。在我们做这个项目的十年间,这个纪念馆的名字就从‘日军馆'变成了‘日本侵华罪行馆',日本媒体非常介意‘侵华'两个字,这之中是不是有政治的原因,我也觉得没关系,因为侵华也是事实嘛。”但矶崎新说绝不会将它做成一个“伤痕累累”的建筑,他想要做的是一个与文化相关、有城市氛围的博物馆, “中日之间的渊源并不只有近代的百年,也许五十年以后中日非常友好,日本侵华罪行馆又变回了日军馆,甚至变成了中日友好馆,都是有可能的。”
采访快结束时矶崎新自己也感到抱歉,说建筑还是谈得少了。这一定不是矶崎新最好的设计,但一定是他最为人津津乐道的建筑之一。前几年有人去参观,曾说这个建筑有自己的“精神气”在里面,可是矶崎新自己并没有给出这么高的评价,在民营博物馆预算控制下进行设计建造,他本身的考虑重点就不在创新、精美、细致、技术这样的层面上,“就是在预算下做一个大的持续百年的展览厅吧,从这个角度上说,应该还是完成了使命的。”矶崎新说得很委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