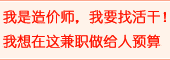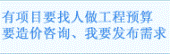Tulips Chen
伊东丰雄:不浸入消费之海就没有新建筑
时间:2013-08-28 15:34来源: 作者: 点击:次
摘要:建筑以惨烈的势头被建起,然后被消费,完全到了恐怖的程度。十年前,不,即使是五年前,在街上走路时,还能立刻认出:啊这个是建筑师设计的楼啊。但是现在不同了。多大程度是建筑师上的作品,多大程度是室内设计或者策展公司设计的,已经完全无法分辨。

一般的杂志、电视、报纸上,热点建筑和热点建筑师也频繁登场。与建筑相关的研讨会、讲座、展览一年到头举办,外国的名建筑师也纷纷轮流来日。从这样的场所传递出来的新鲜内容,被大街小巷中的商业建筑和住宅复制,城市空间从而一天天改变。建筑的世界里也渐渐开始太阳当空照了,建筑师们这么说着,沾沾自喜,也是一下子的事。现在新也好旧也好,巧妙也好拙劣也好,有原创性也好没有也好,要讨论这些已经显得迟钝迂腐。建筑师们陷入了这样浑然一体的,骚动的状态中。假使昨天出现了布料般轻飘飘舞动的建筑的意象,第二天建筑杂志的内页里便已经装满了轻飘飘的建筑。但是建筑开始充满大街小巷并开始流行这件事情,与建筑变得像纸屑一样成为消费的对象完全是两个平行的现象。完全是在五年的时间里,建筑对于社会存在的意义已经改变了。建筑师们自己对此现象的认知已经超越了肯定或者否定的层次。电视和杂志,无论是ID或图像的商业设计和时尚领域,然后连艺术样式,连音乐、电影、甚至文学的世界中,这个现象早已日常化,成为了事实。大概是由于建筑的使用年限较长,又扎根于土地上不动,因此偶尔会认为其不会被消费吧。但是几乎全部的建筑师都被卷入了社会或者说资本急速的循环流动中。表皮化、符号化之类的批评涌现的同时,城市空间却明显以更快的速度在符号化、表皮化。因此,要说这样的状况对于建筑师来说是一次危机,其实并不是建筑师是否生来就是为了否定消费社会的问题,而是建筑师能在多大程度上彻底舍弃只有建筑能够安然避开消费主义的想法。作为建筑师,首先应该有这样的认识。
在这样的时代,即使想要讨论一下形态的好坏,原创性的有无,也完全无从下手。轻飘飘的形态到底是左倾也好右倾也好,什么意义都没有,要主张是自己率先将轻飘飘的形式作为意象,也没有什么意义。重要的是轻飘飘不仅是一种形式,而是像这个时代的氛围、空气一样的东西。包含这个消息的空气像潮流和流行语一样在大街小巷快速传播。无论是哪一家的电视,都播放着同一个偶像明星的同一个旋律,就像所有女性杂志的彩页都充满了同一种风格的时尚,轻飘飘的建筑也将充满建筑杂志的页面,充满时尚名品遍布的街道。这是极为自然的现象。与建筑师关心与否毫无关系。叹惋也好,绝不叹惋也好,建筑早已是这样的存在,且无法切断建筑是社会性的存在这一事实。因此,这是建筑不可避免的道路。此外,社会正在比我们想象中更加坚实、激烈地前进着。所以我对这样的现象不抱任何沮丧的心情,也并不会为此叹惋。我想要关心的只有一个问题:在这样的时代里,建筑还能作为建筑而成立吗。在消费的状况下做建筑,无论如何乐在其中,这个问题也绝不应该抛在脑后。正是由于建筑被同化成时尚,建筑师与室内设计师、文案策划的区别慢慢泯灭,我认为在这样的消费状况中有必要彻底探寻建筑成立的可能性。也就是说,当今建筑存在的框架(topos)在持续、剧烈地变化中,在其边缘,建筑还能作为建筑成立吗,这就是我想要探寻的东西。究其原因,应该是因为我认为,常常在使建筑成立的框架扩展的情况下,才能从边缘上生出十分刺激、充满活力的建筑。因为在名为建筑的竞技场上,亮出并摇晃一下“消费”这个词,多少会产生些崩坏或者膨胀之类的效果吧。从那狭窄的缝隙中,能够产生出什么样的建筑呢,我想确认一下。
有想法的建筑师们都会畅想建筑的本质。但是大多数这样的尝试都太过缺少对于消费最前线的自觉性,换句话说,仿佛对自己的建筑过于信赖。大多数场合,建筑师选择相信自己可以不受社会控制,从而完全依赖形式的操作。要么模拟现代都市空间的错综、混沌、扩散的形态,要么通过古典建筑元素的构成来制造出安定的秩序,两者来回反复。然后两者的绝大多数都会在解构主义或者后现代主义的俗称下,接连不断地前往东京这样的城市空间,然后在巨型垃圾处理场被回收,徒劳一场,浮世若梦。建筑的自律性与艺术性方面的尝试,大概只有到七十年代为止是有效的。的确在当时的城市里刻下空白的美丽的一点是新鲜的行为。由于当时的城市中并没有社会的文脉,通过社会与城市的文脉来谈建筑实在很虚伪,因此反而那些与城市中社会的文脉断开来的,无处放置的形式,其自律的姿态显得异常优美。铃木隆之在《建筑批判》(《思潮》一九八九年第四号)中称这种状况妙不可言。其中提到,“可能激进主义正是从现代主义的停滞和空虚开始出发的。”此外,“我认为激进主义的停滞,并非停滞在彻底发现了空虚这件事情上,而是在无法自如地操纵空虚本身这件事上。联合赤军和三岛的剖腹所展现的,不正是将空虚装满意义的尝试吗。从这一点来说,用高潮来填补空虚的高度资本主义社会,从其对于空虚的认识和操纵法之巧妙而言,可以说永远都是后现代也不一定。”我对这样的批评深感同意。正如最初所述,这几年城市空间已经充满了空虚的记号。美丽的闪耀的空白的一点如今已经深埋在无数的空虚的记号的堆积当中。然后越是要用高潮来填满空虚,空虚越是大幅增加,高潮过后盼望下一次高潮,怀旧之后唤起更深的怀旧,如此巧妙的资本操纵促进系统正全力运转中。但是,表面上的形式主义的蔓延——空虚的符号的堆积场——同对高潮的渴望一同捆绑起来,如此蜉蝣般短暂的城市空间之中,我们除了作为游牧者,尽情玩弄空虚的符号,将符号的再生产作为建筑的尝试之外,并无别的办法了不是吗。就算是这样,也是极为空虚的吧。
我认为,在追问建筑的本质之时,应该从新的城市生活的真实,而不是从形式主义的操作开始。这十年左右,我们叹息于在这样惨烈的消费生活的增幅作用中失去的现实。我们如同毒品成瘾患者沉溺于毒品中一般,感觉在社会中自己的身体不断被侵蚀,仿佛被带入到了幻影的虚构中一样。电视流行的时期,随身听、家用电脑风靡全球的时期都是如此。咖啡吧的大餐桌在年轻人聚集的地方大量出现的时期也是如此,冷冻食品专柜在二十四小时营业的便利店中出现的时期也是如此。所有人都感觉到,电视和家用电脑从餐室夺走了最原始的家庭交流。感觉到了咖啡吧的金属或石制的巨大的餐桌,将烤串店内热烈而粗俗的争论换成了关于炫酷时尚的食物的话题。感觉到了随身听爆炸性的热卖将年轻人封闭在更加孤独的世界。的确我们都觉得,生身的肉体和精神正在游离,失去了生活的真实。察觉到自然,将人类浓稠的血液送入处理厂的生活,沟通正在解体的丧失感,无疑这就是空虚的感觉。一直到过剩,物品越是泛滥,丧失感和空虚越是增加,有想法的建筑师对这样的状况感到愤怒,批判消费,坚持彻底抵抗。年轻的建筑师对此并无感觉,也没有批判,对此的愤怒我也体会到了。如同八束始所叹息的那样(《超越虚无主义》,《新建筑》,一九八九年九月号),建筑系的学生对于生活真实的缺乏,肤浅的时尚的形式主义的追随,对于这些愤怒的感情,我也体会到了。诚实说,这样愤怒的感觉并非从未有过,但是最近却觉得,即使要批判这种状况也无从下手。空虚的消费符号日益增加,有自闭症气质的建筑系学生也在增加,但是开始觉得在其中也许能够看到新的城市生活的真实。就算再怎么要叫自闭症气质的学生更加开朗地生活,也仿佛是关掉电视,叫边看电视边吃汉堡的小孩子和家长边说话边吃饭一样。与其这样,我们其实更应该找到一张能够好好享受汉堡的美味的餐桌吧。与其讨厌咖啡吧的大餐桌,死守在烤串店的柜台,不如在咖啡吧的大餐桌发现新的真实吧。每当我坐在花岗岩或者金属制的大餐桌前,都想要将付着在上面的带来快感的消费符号剥下,做成在宇宙中漂浮一般的无厚度无重量的圆盘一般的餐桌。在那张大餐桌的边上,想要大家一起围着一张大餐桌吃喝的原始的欲求,和顾盼四周,对能够与素不相识的面孔也能喝酒的孤独的欲求混在一起。被置换成了怀旧与潮流纠缠起来的疑似物的存在感。放开这种四不像的状态,向着虚幻得让人觉得恐怖的世界,将物体消除。感觉真实并不在消费的面前,而是只存在于超越消费的彼岸。所以在这片消费之海面前的我们,只能浸入水中,向对岸游去找寻什么,除此之外并无他法。如果只站在海岸边看着,水位只会越来越高,因此无法拒绝游泳,也不能茫然地被海水吞没。
但是,尽管充满空虚符号的消费主义的当代社会将我们的身体变成冷酷的仿生机器人一般,有趣的是我们不断探寻人生最根源的行为的事实。将吃饭这件极为原始却单纯的行为彻底触发的社会真的到了这个程度吗?过度的复杂,过度的虚饰,穷尽想象的界限,消费社会逼近餐饮,穷追不舍。城市中的餐馆每天以难以置信的速度开张,变动。百货商场的食品卖场堆满了亮晶晶的食物,杂志和电视中关于食物的信息,这些完全像希区柯克的《鸟》一样袭击人们,将人们吃个精光。如此这般惨烈。如同吉本芭娜娜的处女作《厨房》及之后的《满月——厨房2》的标题一样,有关吃饭一事,对日常的描写贯穿始终。与故事情节的展开无关,主人公都是在厨房边做饭或者边洗碗边对话。永远都在吃饭。“夜色开始变得透明的时候,我们开始大吃特吃晚饭。沙拉、派、炖锅、炸土豆饼,炸豆腐、泡菜、凉拌鸡肉粉丝、基辅汤、醋猪肉、烧麦……虽然国籍乱作一堆,我们却并不在意地吃了很久,一边喝着酒,全部吃光了。 ”又或是在深夜奔向便利店。
“夜里我睡不着,跑去便利店买布丁,结果进门的地方,刚好下班的惠理子和在店里工作的其实是男生的女生们,用纸杯喝着咖啡,吃着关东煮。我喊惠理子!她就拉起我的手,笑着说,哎呀,离开我们家以后瘦了不少呀。她穿着蓝色的连衣裙。 我买完布丁出来,惠理子一手拿着纸杯,热烈地望着在黑暗中闪光的街道。我开玩笑说惠理子的表情像男生一样啊。惠理子一下笑了起来,说,哪里,咱家的姑娘胡说八道,莫非是到了青春期了。我回答说,我明明已经是大人了,店里的女生都笑了。然后……说再到家里来玩啊,哎呀太棒了,笑着告别了,那就是最后一次见到她了。”毫无顾虑地吃,毫无保留地聊天。实际上是充满生命力地在说话。实际上其中洋溢着丰富的感受力。对人完全信赖。生活在消费主义的正中间,却毫不势利,也没有被消费的洪流卷走,对人类肯定。充满了丰富的崭新的真实。难道做不出像吉本芭娜娜的小说那样具体的、充满生机的纤细的建筑吗,我在某本杂志的专栏这样写了之后,上文中引用的铃木隆之在一起喝酒的地方反击我。两个人都醉到不行的时候,虽然还没开始辩论,但是提到了类似“她的小说的世界观还没有分化形成”的意思。的确,换作亲身创作小说的铃木来说,没有世界观的世界在多大程度上能够作为小说成立,肯定是日日夜夜不停思考的问题。自然也无法忍受对世界观或者文学等等概念缺乏自觉性的少女的文章受到如此无保留的褒扬这件事情。对我来说,建筑的世界中唯独关心的是建筑的本质。因此,要是想芭娜娜的小说一样的建筑出现了,我大概要发出和铃木一样的呼喊了。尽管如此,仅在那么具体的日常对话中,就包含了那么丰富的内容,实在无法不为她的诚挚而感动。
最近为了在布鲁塞尔举办的展览,做了名为“东京游牧少女的包-2”的原尺寸大的模型。其实也应该叫做三年前做的模型的修改版,之前的那个是用半透明的布来表现蒙古包的家的形状,这次用多面体制作了如同太空船一般漂浮在空中的模型。虽然也可以说是更加未来感的表现,但是在这个差别中表现了我心中的城市生活的想象的差别。也就是说三年前,我诚然是很犬儒的。漂亮地委身于时尚的空间中,大吃特吃,在消费最前线享受城市生活之乐,我觉得当时一半的我是对这些抱有憧憬,另一半的我则是无法摆脱自觉性的缺失。但是对于这次的游牧少女,我期待能从未来的城市空间中发现新的真实,开拓具有未来感的城市生活。因此,希望住进去的少女能够拥有芭娜娜的小说主人公一般的感受力。然后去年,仍然是为展览制作了架空项目“地上12m的乐园”,设想了在东京上空漂浮的游牧少女的包,能够在现有的街道地区上空滑翔,在建筑物的屋顶变成阁楼的姿态。这个项目同样是对现实的城市生活稍作加工,是希望能够制作出虽然短暂,但是能吹走怀旧,享受开放的、生机勃勃的城市生活的空间的结果。希望即使是自闭症气质的男生也会被此吸引,而毫不犹豫地尽情享受原始的未来的生活。于是,接下来的步骤就是将如此获得的城市生活的意象转换为建筑空间的任务了。但是,这里既没有什么追求崭新的表现形式的苦恼,也说不上热情满满吧。太过于追求表现力,很有可能陷入形式主义的陷阱,反而会像前述一样被消费掉。总之,最后决定将生活的意象插入既有的建筑空间中。之后将已经闭锁的建筑空间到处开洞,让新的城市的风、空气、光线全部进去。生活的意象仿佛建筑空间的炸药。这样,就能让既有的空间稍稍偏离,变成另外的空间。反复进行这个偏曲的过程中,肯定能在新的城市生活的真实中生出新的建筑。对建筑越是固执,我们越是能乐观地享受,最后也终将超越我们的城市生活。